
T=题名(书名、题名),A=作者(责任者),K=主题词,P=出版物名称,PU=出版社名称,O=机构(作者单位、学位授予单位、专利申请人),L=中图分类号,C=学科分类号,U=全部字段,Y=年(出版发行年、学位年度、标准发布年)
AND代表“并且”;OR代表“或者”;NOT代表“不包含”;(注意必须大写,运算符两边需空一格)
范例一:(K=图书馆学 OR K=情报学) AND A=范并思 AND Y=1982-2016
范例二:P=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AND (U=C++ OR U=Basic) NOT K=Visual AND Y=2011-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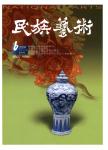
摘要:祭仪歌舞是台湾少数民族艺术的经典表演与呈现。尽管面临社会解组和文化消逝的挑战,其表演形态却能够伴随场景的变动而焕发出蓬勃生机,其文化意涵也随着表演层次和面向的叠加而历久常新。台湾省台东市卑南人南王部落及其周边的年祭圈舞经历着从“圆圈”内到“圆圈”外的转变,进而实现了从部落到剧场的跨越:参与表演的多重主体互动交织成一张表演之“网”,文化持有者和参与者的回馈与反观则构成了一面表演之“镜”,表演的“网”与“镜”交相呼应,再现与重塑了“卑南人”的当代形象,进而探求出卑南人在本土文化焦虑中的创造性转化之路。

摘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作舞发源于云南省红河县阿扎河乡垤施洛孟一带,集歌、舞、乐于一体,起初由哈尼族、彝族共创。随着族际交往范围的扩大,乐作舞传播到汉族、傣族、瑶族等民族中,是典型的多民族共享的民间舞蹈。文章通过分析多民族共享乐作舞的诗性根基、现实条件及价值逻辑,为民间舞蹈的多民族共享机制研究提供典型个案。多民族在增进乐作舞共同性的同时,又能尊重和包容其差异性,使乐作舞成为沟通多民族的艺术媒介和情感纽带。乐作舞个案经验表明,多民族共享民间舞蹈是多民族一体性身份认同的身体叙事和象征符号,是区域性多民族社会团结互助、和谐共处的重要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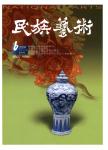
摘要:"托干舞"作为塔尔寺"羌姆"的开场舞段,借以动作、调度、道具、面具这四种舞蹈身体语言,营造了一个有关于"死亡"的大剧场,并围绕着死亡这一哲学命题开展了深入讨论。如同司芬克斯之谜一般,"托干舞"以"边缘处境"的体验方式,让人们直面死亡,体悟人生的有限与短暂,破解了"死亡"的本质问题,深刻探索了"死亡"的价值,以此最终实现了对"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参度与回旋。

摘要:在多民族的中国,从民俗艺术角度研究本土民间演艺,尤其不可忽视少数民族艺术。在山高谷深的岷江上游,诞生在黑水民间土壤中的融合着藏羌文化元素的铠甲舞,展现为歌舞艺术,融汇了宗教情感,体现于仪式行为。从文化结构到艺术形态,从象征符号到展演场景,从身体表现到仪式功能,从族群生活到传统风俗,凡此种种,从民俗艺术角度而不仅仅是纯舞蹈学或纯艺术学角度看,其中都有值得舞蹈人类学或艺术人类学研究者深入关注的许多东西。

摘要: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与该院研究生院舞蹈学系联合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姜宇辉教授讲授“西方哲学史上的身体问题”,期待借此拓宽学科视野,推动舞蹈与其他人文学科的交流互动,以顺应新时代的学科发展要求。也许,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开设这门课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一方面,舞蹈作为一门艺术的形式本身及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当代演进,使得当代舞蹈成为一种“与身体进行开放性交换的体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舞蹈所发生的断裂式变革中,最突出的特点正是舞蹈艺术家们对身体而非舞蹈动作的重视。舞蹈摒弃了以往的技术、审美和风格,转而探究身体自身的智慧、身体的运动机制,以及身体的文化意义和建构主体的潜能,当代舞蹈因此爆发出思想的力量,也因此成为一种建构性的文化实践。另一方面,从学科史角度看,舞蹈研究也因为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理论热潮,以及文化研究、表演研究等跨学科领域的出现发生着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以往强调舞蹈类别和风格的舞蹈历史研究转变为借助各种理论工具展开文化阐释和理论思辨的工作,身体研究正是处在这个转变与其他人文学科相交叉的地带,引起了当下舞蹈研究的广泛关注。舞蹈对于身心二元论困境的破除,舞蹈与生命的紧密关联,以及舞蹈对于人类在技术时代危机中予以突围的潜能,将成为未来舞蹈研究的重要学术话题。舞蹈学,期待更广阔更深入的肉身之舞和思想之舞的共鸣。

摘要:身体记忆是历史积淀的身体意识,它连接着部族的生活方式及精神意念,意味着集体性的心理共构和身体图式。"藏彝走廊"纳西族丧葬仪式舞蹈"热美磋"的动作形态、身体语言,保留了游牧社会日常动作而促成的人体运动动力定型。随着社会的演进,游牧狩猎时的身体元语汇,在仪式场景里经过不断地重复操演,成为舞蹈身体语言。以"■"为形态的身体图式,在仪式场域中被反复呈现,声音、身体和舞动的场景共构了祖先生活的图景,隐喻着亡灵生命的再生。人们在献祭的过程中运用舞蹈身体语汇,表达了历时性的身体记忆,并以动作的隐喻构建着社会元叙事的动力系统。

摘要:在舞蹈生态语境下,舞蹈与环境相互关系、相互作用,舞蹈文化的多元性和传承发展的可持续性值得我们关注。文章通过对云南阿昌族舞蹈生态进行调研、对阿昌族的族源及其历史上客观形成的舞蹈文化的多元性现象展开分析,并以阿昌族的代表性舞蹈"蹬窝罗"为具体的实例,指出了阿昌族民间舞蹈在传承、发展中出现的"趋同性"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及建议。

摘要:本文从舞蹈人类学的角度对巫、傩舞蹈的发生、形成及其流变发展进行了简单勾勒和梳理,并从语源学、语音学和语义学对先秦巫、傩概念多层面的阐释。巫傩是一个多元文化概念即南方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形成的复合体。本文研究证明:巫傩从先秦以驱除疫鬼和疾病的巫术仪式开始,到秦汉时期逐渐演变为一种巫傩舞蹈的祭祀仪式;北宋时期,巫傩舞蹈艺术形态更倾向于本体化、本土化或倾向于戏剧化,明清巫傩舞蹈更朝向于民族化、民间化发展,从而使巫傩舞蹈成为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具体艺术表现形式。

摘要:作为新兴的舞蹈研究领域,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的"民族舞蹈学"(Ethnochoreology)和"舞蹈人类学"(Dance Anthropology)彼此有交叉也容易有概念和认识上的混淆。这两门学科都是从美国率先发展起来的,这亦反映出这些学问在创立之初追随音乐学领域建立起来的"非欧洲主流舞蹈"的研究视角和取向。尽管彼此交叉,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在音乐学领域中这两门学问彼此交融而又各自成型的理论诉求。这样两种学问彼此交叉的现象源于它们在研究对象上的接近和研究方法上的趋同,情况较为复杂。对于中国舞蹈文化的实践而言,这些新兴的学科都给我们带来崭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这些学科概念的认识和梳理,会让我们更容易地看清这些学科的内涵及其差异。

摘要:民族舞蹈学目前的理论基础是将民族民间舞理解为一个与其所处环境密切关联、随着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过程。笔者分别从种族、传统、文化、民族等与民族民间舞密切相关的概念出发,在不同学科的研究基础上,阐述了民族民间舞的不断变化的本质。强调了中国的民族民间舞的研究应当建立在这个对民族民间舞的重新理解的基础上。民族舞蹈学在中国的着陆和发展目前只是一个开始的阶段。当我们讨论某一个民族民间舞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只是讨论这个舞蹈本身,还有它生存的特定环境(这个特定环境可大可小)。如果环境改变了,舞蹈本身一定随之改变。
地址:宁波市钱湖南路8号浙江万里学院(315100)
Tel:0574-88222222
招生:0574-88222065 88222066
Email:yzb@zwu.edu.cn

